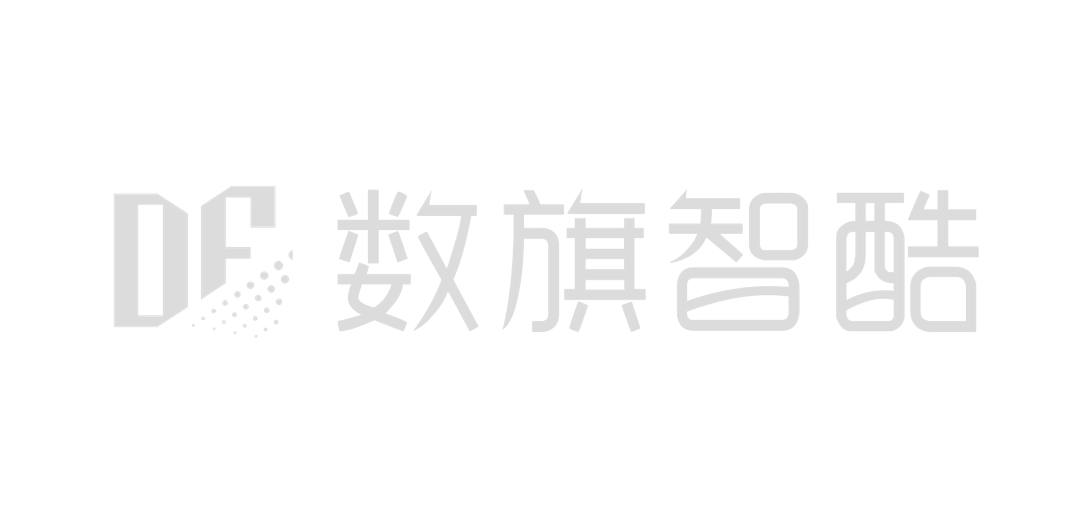2018年4月,浙江省省长袁家军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政府数字化转型是政府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是从量变到质变、从理念到行为、从制度与工具到方法的一个系统性过程,是今年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的重头戏。要加快研究制定政府数字化转型总体方案,明确目标任务,构建框架体系,建立推进机制,把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结合起来,把各地各部门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把社会各界的智慧和力量进一步凝聚起来,营造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良好氛围。
2018年6月,浙江省省长袁家军在一次会议上指出,建设数字政府是遵循“政府理念创新+政务流程创新+治理方式创新+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四位一体架构的全方位、系统性、协同式变革。建设数字政府,根本目的是通过数据整合、开放、共享,为群众提供个性化服务;基本手段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关键举措是以流程再造实现跨部门、跨系统、跨地域、跨层级高效协同;实践路径是构建人机协同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集成应用系统。
以上是目前为止官方公开发布的对“数字政府”和“政府数字化转型”简练、准确与富有时代性的概括性描述。

今天我们究竟需要怎样来理解“数字政府”和“政府数字化转型”?似乎还没来没有权威与客观的官方界定,对概念、内容、目标、方向等均无较为妥帖与恰当的讨论。电子政府、虚拟政府、网络政府、在线政府、智能政府、智慧政府等应该是近二十年出现了较为常见的概念,它们都从不同的侧面、对象、特征和诉求描述了对数字政府的理解,作为一个数字化时代的“盲人摸象”,其实都是从政府的文件数字化、流程数字化、治理数字化、服务数字化、决策数字化等方面的阶段性定义。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现状?
我粗浅地认为大概存在三个原因或心理,一是过去十年新兴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资本狂欢让政府与市场都沉溺于对“造词”与对修辞的崇拜,而没有时间去真正考虑业务与用户,这种对想象力与创造力的透支让大家都羞于对曾经被放弃过的或者视为早已过时的价值认识进行回潮式的翻炒;二是过去二十年的信息化发展其实让整个政府都处于数字化转型的历程中,韦斯特在2001年就撰写了《数字政府:技术与公共领域绩效》一书,介绍政府网站如何影响政府的信息、互动、服务以及民主,而2011年这本书被国内编译出版,今天我们重提“数字政府”与2001年、2011年的数字政府又有什么异同?从PC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在门户网站、搜索引擎、社交媒体等不同模式下,数字政府在不同阶段的价值、特征与核心,我们并未清晰化;三是我们对数字化本身似乎还缺乏理论自信,在蒙眼狂奔的中国互联网黄金二十年,中国市场从copy to china蜕变为copy from china,这个市场有数不尽的经验、教训和进入各种世界级商学院的案例,但唯独属于中国的理论还在萌芽期,而最新出版的《信息规则》修订版中的中国案例似乎在尝试做弥补理论空白的努力。
在追逐时髦与流行面前变得盲从而又手足无措,在技术的牵引力面前显得焦虑而又力不从心,这似乎可以解释当下在各种媒体版面此起彼伏层出不穷的数字政府“改革口号”,口号越新、越怪、越晃眼睛,本质上是一种政府组织面对数字化转型的焦虑符号。


从整个数字化的历程来看,我国的政府数字化转型则从1999年“政府上网工程”之前就已开始,那之前实现的其实是将档案从文件柜里搬进局域网电脑的硬盘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政府数字化转型开始真正进入从信息数字化、业务数字化与组织数字化的轨道中,而互联网在每一个阶段都诞生了伟大的技术革命与商业模式,在信息数字化阶段,以门户、搜索为主要商业模式的PC互联网飞速发展,而政府开始通过建设门户网站理解信息革命,虽然本阶段很多政府网站号称可以“在线办事”,但由于体验不佳、数据不通等问题,本阶段的根本特征还是“信息数字化”,这个阶段强调的两个核心是——信息与系统。
这个阶段十分漫长,一直延伸到移动互联网商业产业的逐渐成熟——2010年,智能手机、微信、微博等硬件的变革与移动应用的出现,重塑了人们对政务服务的认识,以电商、社交、聊天的方式参与和开展政务服务逐渐成为潮流,第三方社会化平台的服务能力得到拓展,移动互联网的“溢出效应”极大地提升了移动政务的参与度、体验度与社会口碑,这是“业务数字化”真正成熟的阶段,这个阶段强调的是——连接与在线。本阶段一直延伸到现在并未结束,因为各地推崇的“最多跑一次”、“不见面审批”还未完全实现。
第三个阶段是“组织数字化”阶段,本阶段是由于海量数据爆发、协同治理的迫切性以及平台化挑战的综合作用,倒逼政府机构必须通过实现组织的数字化转型,才足以应对数字化未来趋势,因为不能给一辆法拉利的发动机装在一辆拖拉机上。这个阶段强调的是——数据与智能。
在“组织数字化”的阶段,以信息、业务、部门、行业的角度来看待数字化的影响与决策都会显得狭隘,必须跳出原有的框架和坐标系来审视“政府数字化”。在一切尚不明朗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从数据、用户和场景三个角度来获得对AI时代“数字政府”的价值认识。
- 数据:From Resource to Power

数字政府本质上是一种数据驱动的组织范式。对于企业而言,“数据即资源”,对于公民而言,“数据即权利”,而对于政府而言,数据正在超越资源、资产的认知范畴,“数据即权力”,数据本身成为一种权力,无论是“最多跑一次”还是“不见面审批”,没有对权力的重塑就无法实现对服务和治理的重塑。同时数据也在成为一种扩张性力量,一种改进政府运作模式的内在动力。
从前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再到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从数据视角来定义人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同时也存在着国别差异,当我们的国家安全部门开始通过IP地址在捕捉不法分子的时候,我们从韩国电视剧《信号》和英国真人秀《潜行追踪》里可以看到——他们最擅长的是利用信用卡消费和取款记录来锁定目标,这说明数据以及数字化在权力运行流程中的生长速度与方式是存在差异的。在前互联网时代,我们基本是以电话、短信和收信信息来定义一个人,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定义一个人的方式包括了IP地址、Email、QQ号码等,移动互联网定义一个人最大的区别是不再以联系方式与静态信息来定义,而是以比如地图导航、网约车、外卖订餐、在线视频等动态的真实移动轨迹,人工智能时代则包括了无人驾驶、家庭机器人、刷脸支付等涉及无人化与生物性信息,更有可能的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将因我们的需求与习惯重新创造出一个“自己”——即AI私人助理。
- 场景:From O to O to O in O

社交才是人类最本质的需求,“社交化”意味着情绪感染、互动高频、价值转换。——数旗智酷
AI时代的数字政府治理与服务的场景均将进一步深化,线上线下的O2O已经不再主流,更值得关注是O in O,即混合现实,虚拟和现实互融,VR和AR的流行将在司法、交通、环保、医疗、教育等领域重塑场景秩序,用AR模拟城市规划、提前预测大型活动交通流量以及公务员考试模拟等,可以有效规避风险,提升效率和体验。当下数字政府的场景趋势需紧密关注三个方向,首先是社交化,一切服务都被社交化和对话框所左右,并且正在向语音交互的方式发展,从政务APP到微信平台,从智能问答机器人到在线客服,“没有社交就没有服务”;其次是AI化,“用户画像”可能正在成为历史,AI机器人对图像识别、自然语言识别的深度学习,“用户”对于政府而言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公众”,而是需求特征完全各异的“人”,不再需要用户画像,而是针对每一个用户进行定制服务;再次,提供无关位置的“无址化”服务,当数据、智能设备、制度规范的准备已经达到临界点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服务效率和体验俱佳的大厅或平台每天的吞吐量不断攀升,不断地发挥“虹吸效应”将需求“中心化”,而无法跟上数字化转型节奏的大厅或平台可能会门可罗雀,直至最终被边缘化或放弃掉。AI时代的数字政府倡导的是一种依托于算法的需求匹配。
- 用户:From People to Everyone

AI时代的数字政府围绕服务、治理、决策与产业(营商环境)主要有四个建设目标,首先是平台政府,数字政府一定是依托于统一平台和服务入口,打造整体政府概念与形象,并能纳入各种社会化资源进行生态化发展的组织模式,比如近日有城市政府已将银行、中介机构纳入平台合作,再造流程,提升公众办事的便捷性;其次是数据政府,通过大数据分析与挖掘实现精准治理、个性服务与智能决策,这是数字政府的本分;再次是云端政府,从政府网站的集约化建设开始,数字政府本身就要求集约化发展,不仅是对资源的集约化,更是对治理与服务能力的集约化,从能力分散走向力出一孔,云端政府是AI时代数字政府的主要特征;最后,数字政府的内在要求是“开源政府”,数字政府一定不是一个封闭的运行体系,无论是平台还是制度,都需要创造社会化力量可参与的API、连接与机制,数字政府的进化是需要依托于数字经济与民间力量的创新与驱动力的。
AI时代的数字政府未来将走向两个趋势,一是公共服务的“软化”,当机器与算法更好地感知与匹配人的服务,我们面对的不是在依靠用户界面、终端和流程塑造的冷冰冰的服务,更友善更具信任更符合人的体验习惯的公共服务产品越来越多,并逐渐成为主流与常态,“软化”是一种算法与数据对服务体验的人性化再造;二是社会治理的“锐化”,所谓“锐化”即是指政府治理机构在面对社会问题的时候更精准更有把握更有能力进行处置,“锐化”是通过机器与数据的学习与挖掘不断提升对社会问题的捕捉与感知能力,然后转化为决策与处置方案。“锐化”是一种算法与数据对权力的数字化建构。
(注:以上内容节选自数旗智酷数字政府实验室《AI时代的数字政府发展指引》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