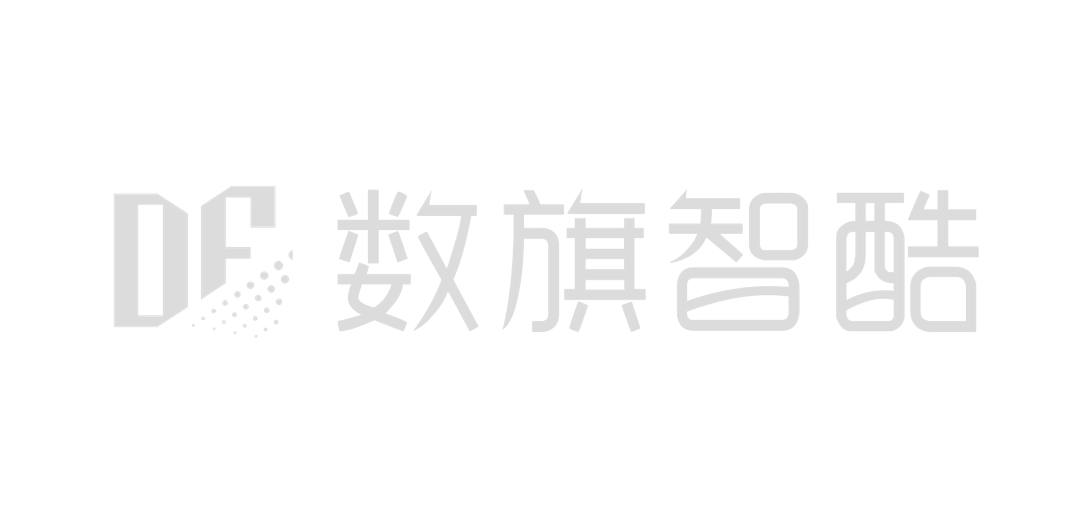作者 唐 鹏 数旗智酷创始人
来源 数旗智酷数字政府实验室
2020年无疑是中国数字政府发展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一年。
根据《2020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电子政务发展指数排名已提升至全球第45位,比2018年提升了20位,其中在线服务指数由全球第34位跃升至第9位,迈入全球领先行列。这个排名与成绩表现标志着过去两年在数字政府领域的高歌猛进,正在使中国获得与改革发展绩效努力相匹配且实至名归的成绩。并且,我们不应该浅薄地将这种影响局限于“数字政府”本身,而更应该看到:以移动互联网、数字经济、放管服改革等混合驱动与建构的治理理念、治理模式、治理能力的中国方案正在影响全球。
站在十四五的门槛上,我们应如何理解改革开放进程与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的数字政府?
首先,从政治层面而言,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所取得的瞩目成绩,本质上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并行趋势下的经济注脚,当以政策、资源、土地、劳动力等传统市场要素为驱动的市场红利逐渐遭遇瓶颈,以数据资源共享、保护、确权和交易的“数据市场经济体制”将成为新的发展动力。因此,梳理数据资源的权利谱系,规范数据产权治理,无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杭州的“数据价值交易”、深圳的“个人数据权属”到上海的数据开放共享“豁免原则”,其背后都是基于数据要素的改革创新。
其次,从经济层面而言,从各地的营商环境优化创新与“抢人大战”可以看出,城市“落户”的政策底线已经由“买房落户”下降到“租房落户”、由“三年社保”下降到“一月社保”,可见依附于传统户籍制度的治理杠杆越来越短,短到已经无法撬动一个被数字化解构得近乎面目全非的世界。而以i深圳、i厦门、穗好办、苏周到、我的南京、我的长沙等城市超级App为主要平台的城市公共服务数字化供应中心,其创新特色与供给能力正在一座城市成为“网红”的理由或成为一座吸引年轻人趋之如骛的“数字黑洞”。但是,撕裂的、折叠的现实随时都在发生,有的城市可以通过城市超级App用5分钟即可办完落户在家里坐等新的户口簿,而有点城市依然需要早上六点多排队去线下大厅交社保。
再次,从社会层面而言,作为一个从农耕社会、乡土社会中逐步迈入工业化、数字化的国度,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城市化”或许都将是中国社会转型值得长期关注的主题,从“村庄里的中国”发展成为“社区里的中国”正在成为大势所趋。而值得期待的是未来市民将如何同时共存于城市空间与数字空间,数字政府将通过在线治理与服务的规模效应助力城市群的“无边界”发展,还是进一步抽空弱势城市的劳动力与资源,形成“数字虹吸效应”使数字鸿沟越拉越大?自从国家层面发布老年人使用智能服务的有关文件后,从广东开始的各地适老数字化服务行动正在开展,而背后我所看到的是过去十多年政府网站“无障碍服务”建设的彻底失败,从而间接导致移动互联网与智能设备带来的老龄化“数字贫困”浪潮显得如此迅猛。同时,这也意味着:政府数字化转型是一次全社会的数字素养启蒙与能力养成革命,一个都不能少。
最后,从技术层面而言,“机器”作为一种被动使用的工具的时代已经渐行渐远,正如《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所呈现的那样,具有自我学习能力、行为目的、情绪反应、令人上瘾的技术环境正在形成。“新人机关系”将革新“使用与被使用”、“奴役与被奴役”的人与机器的“不平等历史”。在数据与算法加持下的具有自主行动能力的智能机器,如何可信、有益、可控地社会伦理和数字伦理的框架内行事,我们的社会意义系统如何赋予机器作为新社会角色的责任、权利与义务?苹果CEO库克曾表示,相比于担心“机器像人”,他更担心“人像机器”。当数字化将原来充满冒险、新鲜与未知的现代社会的一切都进行我们耳熟能详的“程序化”、“规范化”与“标准化”,那么,在稳定、可靠、没有任何惊奇的被价值锁定的流程中,人的存在意义呢?
新冠肺炎病毒疫情的出现,对中美两国的政府治理与政府数字化转型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Governing在近期刊文指出,特朗普政府在疫情期间作壁上观、无所作为的表现,导致联邦政府完全放弃了自身履职而丧失权力扩张的机会。而这将深刻地改变联邦政府与各州之间的府际关系。中国政府则恰恰相反,以数字政府建设为契机,通过疫情防控服务平台、健康码、大数据流调、企业复工复产等系列措施与政策供给,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空前地锻造和加强了自上而下的、从权力中枢到社区基层的统一的权力运行机制。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疫情对不同政府体制、意识形态及社会秩序的影响是割裂的。对于中国而言,疫情在加速面向数字化的转型以及社会凝聚力与共识的提升。全球疫情防控的表象是政府控制疫情的能力与决心,背后是数字领导力构建。
科技公司与大型互联网平台在中国数字政府建设与疫情防控中充当着重要而关键的角色,不仅成为中国数字政府发展水平快速跃升的重要变量,也成为提升疫情防控效率与社会治理水平的推动力量。但是,在“互联网下半场”的声音逐渐微弱、“去中台”逐渐成为一种潮流的当下,“反垄断”一夜之间成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焦点话题。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于2020年11月在《外交事务》上与人共同撰写的《如何从大型科技公司手中拯救民主》一文中指出,与传统公司不同,数字领域的公司不争夺市场份额,它们争夺的是市场本身。作为公共属性与商业属性逐渐弥合的大型互联网平台,近年来在数字政务领域的发展,背后即是政府机构向商业平台让渡部分治理职能的事实,比如个人办事、营商服务等。而大型互联网平台之所以积极参与这部分事务的原因,除了进一步挖掘目标用户以及流量之外,更在于其为优势业务搭建起来的数字基础设施可以通过边际效应递减而可靠地提供服务,优势业务的高额利润也可以补贴其暂时无法实现盈利的部分。现在存在的一种“不确定性”是:假如平台型公司的规模化利润大幅下降,那么,寄生于大型平台的公众号、小程序等移动政务服务平台未来如何生长?参照2020年底广东、浙江、北京、上海、河南等省市发布的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数据,如果当用户快速增长的窗口逐渐关闭,平台的利润又无法补贴,那么,所谓平台的规模效应、用户思维带给数字政务的下一步会是什么?这一切的最坏结果都存在最小的可能性,但并不意味着没有可能。
杭州的“人脸识别第一案”宣判了,媒体将之成为“没有胜诉的胜诉”,原因在于法院判决作为被告的杭州野生动物世界赔偿利益损失,认为拍照收集其面部特征信息等方面不构成欺诈,仅支持删除面部特征信息,删除指纹等身份信息的请求没有得到支持,并驳回了其他的诉讼请求。从判决结果来看,这就意味着野生动物世界可以继续采用仅能通过人脸识别入园的“霸王条款”,强制刷脸的情况得不到任何改善,他们反而会更加理直气壮地强制年卡用户刷脸。这可能就是我们需要重新理解数字化的原因:当“刷脸”被修饰为一种“数字优等阶级”才能享有的权利,通过制造“数字红利”的幻觉来麻醉人,让人失去对个人隐私泄漏和权利被剥夺的痛感与知觉,从而在一种缺乏有效监管的环境下达到一种对个人权利的粗暴干预,并使社会个体处于一种极不安全、也未有评估的风险之中。2020年11月,天津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天津市社会信用条例》,在全国首次公开禁止采集人脸识别信息,旨在规范技术应用、保护个人隐私等。
我们对隐私的定义、监管以及重新审视将会改变未来的社会治理模式与公共服务范式,并且,必将被改变的还将包括我们的肉身。《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表示,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数据可以检测到我们的“皮下信息”的分水岭时刻,过去的技术只能从我们的身体外部获取数据,而现在的技术则可以从我们的人体内部获取数据,从大脑和身体里获得数据,拿到你的温度数据、血压、大脑的反应,甚至一些生物的表征。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剑桥分析”公司在Facebook上的行为之所以受关注的原因——在你没有知觉的情况下,影响你的价值选择,并促使你做出行动。这种“数字催眠术”的存在,将数据公司置身于一种“教唆犯”的角色。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研究员吴伯凡认为,“隐私”在过去代表“我不想让你知道的信息”,而今天的“隐私”正在成为“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但机器可以通过数据、算法比我们自己更了解的信息”。这一点无疑是令人沮丧的,2016年,笔者提出“数据人”——即由人在数字空间的打车、外卖、住宿等动态轨迹的在线行为数据以及生理数据构建的比特化的“数据自我”。现在看来,这个“数据自我”正在成为一个脱离肉身与精神被人控制的“自我”——“硅基自我”背叛了“碳基自我”。
2020年11月13日,中央网信办官方微信“网信中国”发布了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治理工作组《关于35款App存在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的通告》,其中,爱山东、皖事通、鄂汇办、市民云、宁归来、爱城市网等政务服务及城市服务类App涉嫌违规收集用户个人信息被点名。从近年来移动政务的发展生态来看,我并不认为涉及个人信息违规收集使用的问题来自政务服务App的管理机构意志,从我们所调研过的上架Appstore或安卓市场的政务服务App版权信息以及用户评价即可看出,在政务服务app建设和运营上,个别政府机构实际成为了技术厂商的提线木偶,他们用一套被专业主义包装过的话语体系让未经过严格训练与审核的政府机构相信:获取任何信息都是应该的,获取任何数据都是为用户好的。2020年10月,刚结束征求意见的《网络数据处理安全规范》要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工作结束后,指定机构应在60天内或者国务院相关部门规定的时限内,删除事件应对中已收集、调用的个人信息。“删除”——作为一种限制和约束信息采集权力与影响无序扩张蔓延的“回退机制”,恰恰体现了数字治理相较于传统治理的差异之处,在传统治理视野下,一座桥梁、一条高速公路一旦开工建设,其在公共领域就将产生不可挽回的影响,而数字治理在系统、平台、数据、算法的建设方面是可以实现有限控制甚至进行纠偏或挽回影响的。
作为城市化率超过60%的国家,从市民参与城市治理的能力、机会与空间而言,中国的城市型社会却是正在崛起的蓄势期,而“同城通办”、“跨省通办”、“全国通办”等将是推动城市型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杠杆。历史学家秦晖在其著作《田园诗与狂想曲》中提到,以畜牧业为支柱产业的新西兰没有被质疑是否为“市民社会”,而全部人口生活在城市的沙特阿拉伯却不是“市民社会”。同样,可以连接5G网络、操作智能手机、使用移动支付在线打车网络外卖等数字服务,或许并不意味着进入“数字社会”,而只有具备参与数字社会的议程设置、规则设计、权利建构的能力与机会,才算真正进入了“数字社会”。拥有政务服务平台、大数据平台、数据开放平台等数字设施,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方式去开展治理和服务,并不意味就是“数字政府”,只有建立一个符合数字伦理的决策秩序、政务文化、权利观、隐私观的组织才能称之为“数字政府”。
《十四五规划与2035远景目标建议》的“治理”一词出现了51次,首次提出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我们无法准确估计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治理技术与组织技术对未来社会进程的影响,但健康码、人脸识别、算法推荐等带给我们的便利、伤害以及伦理思考,让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从“电脑儿童”到“算法儿童”,我们需要更理智、清醒与批判地接纳未来。(完)